
这些年来,人类见证了许多职业乃至行业的消失或正在消失。但也有一些职业,看似高大上,甚至被视为永不会消失,实际上却呈现“隐形消失”的状态,在谁都想不到的情况下面对困境。在美国学者赫布·柴尔德里斯看来,大学教师就是这样一个职业:
“曾经身负重托,为培养干练自信的下一代画上点睛之笔的大学教师,却被认为不该享有工作保障和健康保险,也不该比便利店的员工获得更多报酬。”
如果要拿一个行当来类比大学教职,最恰当的或许是大多数人都无法想象的外卖员,因为在美国,大学教职的分配逐渐零工化。如果将这些教师的上课时间、备课时间和课后工作时间全部计算在内,收入甚至还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1975年,美国只有30%大学教师属于临时或兼职岗位,但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超过50%,如今更是超过70%。曾经以终身教职吸引人才,长期插根校园从事研究和教育的大学教师职业,竟然渐渐被兼职人员所主导。
赫布·柴尔德里斯在《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中这样写道:
我们像抛弃全科医生那样抛弃了大学教师:异常丰厚的酬劳给了专科医生,却把绝大部分医护工作交给了准专业人员。
我们像抛弃出租车司机那样抛弃了大学教师:降低行业门槛,允许拥有最低资质、对收入不抱期许的任何人加盟。
我们像抛弃媒体撰稿人那样抛弃了大学教师:重新下定义——把作品改称“内容”,把作者改称“内容提供者”。
我们像抛弃本地汽车修理工那样抛弃了大学教师:行业体系和规章制度复杂到必须依靠庞大的技师团队和专业设备。
我们像抛弃簿记员那样抛弃了大学教师:数十年不变的偏见,认为女性无法胜任;当她们入行后用事实证明女性也能做好时,这一职业就开始遭到贬低。
赫布·柴尔德里斯继而总结道:一切不过是“重新下定义”,几番运作之后,大学教师成为校园里的局外人。而作为一种职业,它正以细微、隐秘但又明确的方式渐渐消亡。
这实际上是美国版的“青椒(指青年教师)之困”,也是职业幻灭感的大学校园版。那些踌躇满志,认为将迎来人生新起点的博士们,不会想到自己的执教生涯早已被预设为机器化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有早已确定的课程大纲,有处于最低水平的时薪,有不具备任何保障的合约。前两年中国高校的“非升即走”曾引发热议,美国同样如此,许多拥有博士学历、看似前途似锦的年轻人,沦为非升即走的不稳定劳动力,担任着临时化的教职,焦虑可谓前所未有。
这种困境并非单纯的就业问题,正如《学历之死》中所总结的那样,美国博士人才供应过剩,才导致大学教职竞争激烈,青年教师进入学术圈的几率相当低。而且,博士生的培养模式出现问题,他们无法胜任其他职场工作:
“尽管兼职教师和博士后研究人员确实可以离开高校,投入制药或金融行业(收入总比当个教授来得多),但是,那种在优质的博士教育过程中训练形成的思维模式,并不适合大部分职场环境。”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大学教育,因为大学本身就有着象牙塔的一面。赫布·柴尔德里斯写道:
“商业领域奖励的是‘专业性’——那种你知道你能将事情做得又快又稳妥的能力。而学术领域奖励的内容刚好相反——那种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那种对现有知识和现有做法的不满,以及重新审视自身认知基础的冲动。之所以把学术型博士学位称为‘哲学博士’是有原因的,因为不管什么专业,都是以拥有批判精神为目标来训练博士生的,使他们带着玛莎·格雷厄姆所形容的‘一种古怪而神圣的不满、一种受到祝福的不安’遗世独立。这种不满,与银行和保险经纪公司的职场氛围格格不入,它既不能应付季度性投资总结报告的要求,也无法适应超市或政府办公室的管理工作。”
大学教师面对的生存困境同样也不仅仅是大学的问题,调查显示,过去十几年里,大批年长员工仍然活跃在原先的岗位上,使得年轻人很难获得机会,几乎每个行业都是如此。高校教师领域之所以特别明显,是因为年长的教师都享有终身职位,年轻人的入场门槛更高。书中写道:
“如今,成为一名终身制教师的过程无异于成为一名职业冰球选手。你得从4、5岁就开始一路过关斩将,在体育发展联盟中脱颖而出,为全美青少年赛队效力,或许还得考上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冰球项目的四大盟校才行。你的竞争对手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人生优势,而你必须找到能与之势均力敌的某种方式。”
对学者的要求也一样,赫布·柴尔德里斯写道:
“你得出生于书香世家,顺利考上名牌大学的本科,然后攻读名校的博士学位,在这期间不能因为工作或其他某种冲动严重耽误求学进度。这还意味着,你一拿到博士学位,最好能立即成为科研项目的助理,以共同作者的名义发表论文,并得到主要科研资助机构的认可;而不是立即参与助教工作——这只能说明你成了一名默默无闻的教学服务人员。一位30岁左右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自然会得到经历相仿、条件相似、同样幸运的同行的认可。”
要实现这种层层跨越和无缝连接,难度极大,不仅仅需要个体努力,很多时候还需要家庭背景和运气。“不论在哪个阶段,这一选拔机制都像是一档智力竞猜节目,不断向参赛者提出新的挑战,而他们也能在挑战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优缺点。这是一个覆着保护膜的虚拟世界。”
但事实上,这一切终究是幻象。一代代年轻精英沉浸于这一系统框架中,渴望被评价,也习惯俯首听命。书中告诉人们,美国临时教师规模的扩大,伴随着的是按需而定的宗旨,它是一种标准化运作的产物。也是资源流向的见证。因为等级的存在,不公也如影随形。金字塔底端的助理教师承担了最多教学任务,次多的是全职非终身制教师,而全职终身制教师反而是教学工作量最低、薪资最高的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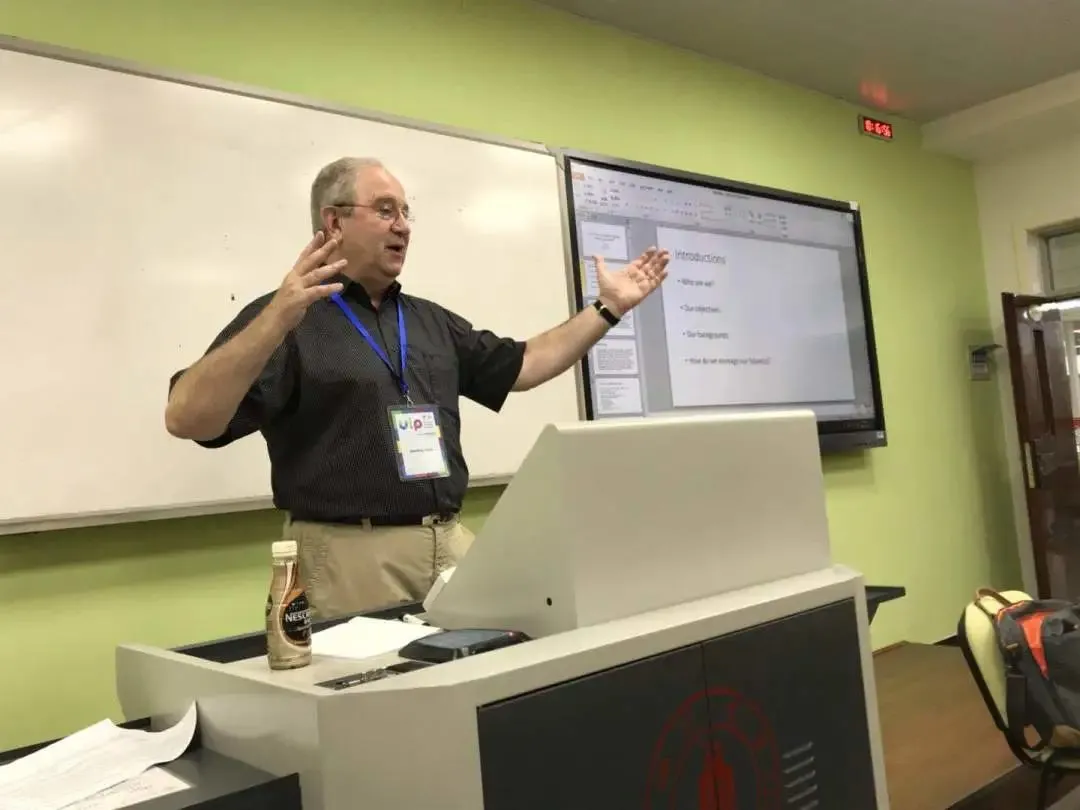
与此同时,终身教职的比例越来越低,书中写道,美国各院校本世纪初的终身制教职员工比例从1976年的45%下降到25%,如今还在继续下降中,大多数非终身教职人员的续聘机会十分渺茫。
教职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也会合流,比如性别不平等。在美国,大学教师身份长期以来都是体现男性专业知识的象征,也是专业人士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这个角色在功能性上瓦解时,它的性别特征也随之模糊。大学教师变成了支持性的角色,更多男性教师被更愿意支持学生、与学生沟通交流的女教师所取代。但这反过来又加剧了不平等,因为女性教师始终处于收入较低、地位不高的境地。
按照美国2013年的数据,在职教授中的男性占 69%,副教授中的男性占56%,助理教授的男性占48%。由此可见,近年来新入职的助理教授层面,女性占比已经明显高于过往。但它未必是性别平等的证明,因为非终身教职中,女性占据了更大的比重,她们的上升空间更为狭窄。她们之所以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仅仅是因为大学教师在功能上的转变,更加趋向于服务性,同时,这份职业也因为按需而定的现实,缺乏足够保障。或者直白点说,美国大学女性教职人员的增加,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成本考量,因为她们工资更低,而且不怎么占用未来的上升渠道。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即“对女性作为个体劳动者的歧视减少,但当女性入行之后,职业歧视则会增加”。一些看似推动两性平等的手段,在真正实施后,又加剧了不平等。并非只有高校领域如此,调查显示,进入男性主导领域的大学毕业生,起薪远高于那些进入女性主导领域的大学毕业生。律师领域也很类似,2/3的律师是男性,但85%以上的律师助理是女性,这意味着在律师领域,女性的上升渠道和在大学里一样狭窄。
同样逻辑,当一个“临时工”竭尽全力、战胜无数人、获得终身教职后,他们也会成为目前高校体制的捍卫者,继而使得这种机制更为固化。
终身教职和临时教师的分化,不仅仅在高校内部造成了隔膜甚至阶层,还影响了高等教育。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生,因为所面对的教师不同,接受的教育也有着极大差异。完全没有时间进行学术研究的临时教师只能充当零工式的教学机器,仅仅为学生提供“课程商品”,而且全社会的实用主义驱动,更加使得高校教育从启蒙转向“实际”,无论学校还是学生,目标都变成了就业。正如有人所评价,“学生以及家长是购买学分的消费者,文凭成为打开就业市场的敲门砖,知识用完即弃,理想遥不可及,校园里满是赶时间的人。”启蒙理念下的“个性化”也变成工厂式的标准化生产,进一步加剧社会阶层固化。
1940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发布了《1940年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制教职原则的声明》,其中表达了终身制教职的基本理念:
研究自由是探索真理的基础。教学方面的学术自由对保护教师教学权利和学生学习自由权利至关重要……终身制教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手段,具体包括:
(1)教学、研究和校外活动的自由;
(2)足够的经济保障,使该职业对有能力者(不论男女)充满吸引力。
出于学术自由和经济保障的考虑,设立终身教职制度,对于院校成功履行其对学生和社会的义务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这不仅仅是一种要求,也是理想。支持者会将第一项条款视为真理,因为学术自由意味着思想的多元化,当高校乃至社会包容这一切,就不会因为无法容忍异端而迫害知识分子。但反对者则无法容忍“永不会被解雇”的特权。
不过不管怎样,在只有不到5%的成年人口拥有本科学历,大萧条导致的失业阴影仍然人心有余悸的当时,这种对高校教师的保障是一种社会需求,也是人心所向。但到了今天,这种理想化确实有些不合时宜,因为有能力的人越来越多,却大多数被排除在终身教职之外,因此制造了更大的不公平,也成为美国社会面对的难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