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虎妈”的另一种读法
——狐狸,还是刺猬?
文 | 田雷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01
兄弟我在耶鲁的时候,也是见过虎妈的。

兄弟我在耶鲁的时候,也是见过虎妈的。
那时候,蔡美儿教授还没有虎妈的名号,不过也早就是名动学界的白富美。去美国之前,我就读过她的书,出版于2002年的《起火的世界》让她一鸣惊人。虽然说是初次展示学术羽毛,蔡教授却表现的虎虎生威。她在书中的观点石破天惊,指责西方国家在后冷战时代大搞制度输出,却弄得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烽烟四起,结论是:自由市场民主非但不是历史的终结,反而造成了一个“World on Fire”。一年前“9·11”恐怖袭击,让1989年后风生水起的历史终结学派声名扫地,却让蔡教授可以在书中大大方方地讨论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Why They Hate Us)”。[2]等到2007年,当蔡教授出版她的第二本书《帝国之时代》时,我已经是她的粉丝。[3]
作为粉丝,在耶鲁那年没能选修蔡教授的课,难免遗憾。记得她那年只开设一、两门研讨国际商事交易的课程,即便要追星,面对这些非我专业的高大上课程,我也只有退避三舍。“2009年6月29日,我开始写作这本书……书的前三分之二,只用去我不过八周的时间”,现在想来,当我在耶鲁法学院院外的“墙街”同蔡教授偶遇时,她大概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第三本书,就是2011年初由企鹅出版社推出的《虎妈的战歌》。[4]那时我已回国任教,还记得此书中文版几乎是同期推出,蔡教授著述返乡,这一次没有一点儿“时差”——只是中文首版被修改为《我在美国做妈妈》,也许是出版社自作聪明,但却弄巧成拙。《虎妈的战歌》,不仅一时洛阳纸贵,在商业上取得空前成果,更重要的是,它成功挑起一场关于中西育儿方式的大论战,蔡美儿教授也由此名动天下,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知道“虎妈”这个名号,虽然未必清楚所谓的“the tiger mother”,原来是一位任教于耶鲁法学院的华裔女性教授。
但时常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人们为虎妈买单,但并不为蔡美儿教授买账。
02
为什么知识分子不喜欢虎妈,读后随手就是一个差评,曾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况明明是:一位华裔女子,出生在父母一代由菲律宾赴美的移民家庭,小时候还曾因讲英语有口音而受到身边同学歧视,现在却成为耶鲁法学院的讲席教授,驯服了同在耶鲁任教的宪法教授“虎爸”,她的两个女儿,《虎妈的战歌》里的主角,先后从哈佛大学毕业,这种经过个人奋斗而走向成功人生的故事,正如虎妈所讲述的,不正是中国知识精英曾经趋之若鹜的美国梦吗?若是如此的话,为什么当虎妈活出我们的梦想时,我们反而觉得难以下咽呢?为什么我们可以空谈一个梦想,但却无力招架一个由此梦想所生成的现实呢?也许,蔡教授在书中表现得并不是那么温良恭俭让,反而虎得有些咄咄逼人,甚至不近情理,但这原本就是蔡教授对虎妈角色的人设,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为何对这位成功人士如此苛责呢?说到底,在很多方面,她只是比我们这些人做得更到位,说得更透彻,要是我们因此而对虎妈有所保留,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不忍心再欺哄,但愿你听得懂

让我先从《虎妈的战歌》开始,再一本本给蔡美儿教授算算账。《战歌》之所以引爆全球书市,当然要归功于它的姿态鲜明,走在政治不正确的路线上,却还能如此理直气壮。一个出版上的细节,也许主要是商业操作的手法,对这本书风行全球可以说功不可没。在《战歌》面市前夕,《华尔街日报》刊发了虎妈的头条文章《为什么中国妈妈更好?》,[5]这样的观点当年一抛出,全美一片哗然,由此引发的争议成功地将随即出版的《虎妈的战歌》推到舆论的风口。就如同现在要想方设法来它几篇十万加,才是商业成功的必由套路。同这篇先期放出的宣传文相比,印在《战歌》书封上的一段剧透文字,却有意识地保持某种文化中立的姿态,读起来只落个暧昧不明的印象:“这个故事,关系着一位母亲、两个女儿、以及她们的两条狗。原本,故事意在讲述,为什么中国家长在养育孩子上要优于西方父母。但最终成书,它却围绕着一场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光荣的滋味转瞬即逝,而我却被13岁的女儿所挫败。”
《战歌》既然如此唱响,那么母女之间的对抗就发生在文明冲突的语境内,要宣扬中国为人父母者的教养方式,蔡教授就要制造出中西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比方说,“西方父母尊重孩子们的个性,鼓励他们追求发自内心的热爱,支持他们的选择……与之形成对照(By contrast),中国式父母相信,保护孩子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面对未来做好准备,让他们发现自身之所能,为他们武装上技能、工作习惯以及内在的自信。”[6]这种在中西方之间反复不断的“by contrast”,正是支撑起《战歌》情节不断延伸以及矛盾激化的逻辑主线。在蔡教授笔下,虎妈的教育方式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刻画着中国父母的家长作风,另一方面则是,非虎妈者,即西方父母也,这种为了冲突而冲突的中西脸谱刻画,当然难以经得起硬社会科学的检验。书之将末,虎妈又一次挑逗西方读者的神经:“我不愿意屈从西式的社会规范,虽然政治正确,但却是如此愚蠢,而且在历史上也从未扎根……非要说,我认为美国国父们怀有中国的价值观(America’s Founding Fathers had Chinese values)。”[7]凡是虎妈做派的,就都是中国的,虎妈之粗暴是如此刻意,在中西方之间乱点鸳鸯谱,西方读者不反弹才怪!
但为何中国读者也不买账?现有耶鲁法学院教授一位在西方兜售中国教育之道,何妨把虎妈也算在中国模式的阵营内,得来全不费工夫呢?为什么非要说不呢?打量一下蔡教授,再读一读《战歌》第四章“蔡氏家族(The Chuas)”,读者大概会有发自内心的质疑或困惑:凭你也能叫中国妈妈?看这位蔡姓女士,出生在美国,父母及其家族都生活在菲律宾,要往前数好几代,祖上才是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的客家人,嫁了个犹太男人,生了两个混血女儿,若是在西方也罢,蔡教授有着黄皮肤和黑眼睛,但当《战歌》漂洋过海来,面对中国读者,虎妈何以主张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之所为,就是中国育儿之道呢?这个问题在这里提出,并不是要刁难虎妈。想想看,《战歌》在书封上即有开门见山的交待,本书的主角是“一位母亲、两个女儿、以及她们的两条狗”,这里的“两条狗”是什么鬼,要是问一下中国人,那么他们必定会问,爸爸去哪儿呢?这种讲故事的方法,真的是中国的吗,还是首先要迎合这本书从一开始就要诉诸的西方读者,因此不过是东方主义的又一次营销而已?
若是继续揣摩他们的心理,恐怕还不仅如此

追溯《战歌》问世时,虽然只是短短七年之前,但虎妈的读者当年就心态而言,却仍停留在上一个时代的尾巴。那些年,我们的中产阶级父母正在乐此不疲地学习西式教育,以之安排自己的育儿之道,他们憎恨之所向,以及媒体火力所要全力绞杀的,正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基础教育。据称,这种以高考为最终检验标准的教育体制只会培养出高分的低能儿,家长要是有本事,就要让自己的孩子逃离高考——到美国去!虎妈在中国的第一波读者,基本上也就是这些做着美国梦的中国中产父母。他们以某种西式教育理念马首是瞻,正像模像样地推行着以快乐为本的教育,也因此,虎妈战歌唱的越响亮,读者心里也就越嘀咕,因为她在书中的每一次胜利都是对读者三观的一次打击。
想一想《战歌》的中文版:《我在美国做妈妈: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8]从“虎妈的战歌”改为“我在美国做妈妈”,国内出版商做了用心良苦的改动,看似出入不大,但整本书的要旨却被改头换面,原本是在西方宣讲中国妈妈的管教之道,中文版却成为了美国精英的育儿经,虎妈的中国身份在中文版的书名中早已消失无踪。据说蔡教授因此对这一版大为不满,身为耶鲁教授以及曾经的哈佛学子,她当然不愿意看到自己被改头换面,也不相信自己的作品非要被包装成“哈佛女生”才能卖得动。但在商言商,“我在美国做妈妈”在2011年显然更能打动人心,让中产父母心甘情愿地为之买单,看一看耶鲁法学院的教授是如何(相夫)教女的。时至今日,我们也许可以说,《战歌》这本书来得早了一些,现如今的中产父母都是“虎妈”了,他们当年对虎妈表示呵呵时,很难想到会有今天。《虎妈的战歌》,在中国是一本属于2018年及以后的书,时间还给虎妈一个公道,而历史的进程也让曾自以为是的中产家长尝到伤筋动骨的教训。原来,他们从来没有掌握文化的领导权,只是随波飘摇的海草而已,不到十年的时间,他们就从快乐的素质教育理念消费者,被社会现实逼迫成中国的虎妈虎爸,那些当年向他们兜售快乐教育的人,现在转而贩卖焦虑,做的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我不忍心再欺哄,但愿你听得懂。”[9]
03
商业上的成功只能证明作者的媚俗

继《虎妈的战歌》在全世界起火之后,蔡美儿教授片刻没有耽搁,2014年初就同“虎爸”鲁本菲尔德教授联手,推出了《三件法宝》。这本书的副标题延续了蔡教授前两本书的命题风格,用“how”引出问题,以此打开读者的好奇心。《起火的世界》的问题是,“为什么输出自由市场民主,却收获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帝国之时代》则追问,“为什么超级大国可以崛起至全球霸主,它们又因何衰落”;这一次,虎妈虎爸向读者抛出问题,“为什么三种看似不可能的特征,却解释了文化团体在美国的成功和失败”。[10]
原本,虎爸就并非《战歌》里唯唯诺诺的为人夫者,对女儿只讲放任自由的为人父者,他在宪法学研究上成就斐然,此前也曾出版过两本成功的小说《谋杀的解析》和《死亡冲动》。现在,虎爸以犹太人的身份加入“战歌”,也就让故事从一个中国式家庭扩展至某些“文化团体(cultural groups)”。虽说《战歌》的现象级成功难以复现,《三件法宝》作为“战歌”之延续,还是让虎妈在版税上赚了个盆满钵满。
这大概也能解释为什么虎妈的同行向来对她颇有微词。他们心里的潜台词应当是这样的:真正的学术书一定是为极少数人而写的,往往曲高和寡,反过来说,商业上的成功只能证明作者的媚俗,不过是投大众所好。简言之,学术和市场不可兼得!一本接着一本,从《起火的世界》(2002)、《帝国之时代》(2007),到《虎妈的战歌》(2011)以及《三件法宝》(2014),再算上2018年刚刚出版的《政治的部族》,这一路算下来,蔡教授保持着四年一本畅销书的节奏,在学术界内外名利双收,又不受论文发表和引证的考验,怎能不让人羡慕嫉妒恨呢?
如果一本本来算账,蔡教授的写作跨度可谓是令人叹为观止:下笔千言,但每本书的主题相距又何止万里。《起火的世界》是蔡教授的头生子,严格说来,也只有这本书是她在所处领域的专业之作,厚积而后薄发。理解这本书的意义,首先应明确它不是“9·11”事件发生后临时抱佛脚的应景之作,在飞机撞向“双子塔”后,加入政治正确的洪流去反思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非但不需要横眉冷对的勇气,其实只是狐假虎威而已。《起火的世界》虽然出版于“9·11”事件一年后,但蔡教授的主要论点早在1998年就已经和盘托出,白纸黑字的论断,可参见她发表于《耶鲁法学杂志》的长文《市场、民主和种族:迈向法律与发展的新范式》。[11]在书中,批判的武器从一开始就对准了冷战后妄言历史终结的观察家,福山先生当年可是鼓吹自由市场民主解决一切呢,著名写手弗里德曼甚至到2005年还出版了《世界是平的》,也同样风靡全球了啊,对于这些很傻很天真的论调,如Elle杂志(中文版为《世界时装之苑》)的评论,蔡教授的这本书不亚于“一记响亮的耳光”。
为什么在众人皆醉的历史进程中,蔡教授却能独自清醒,她之视野所及,又有什么是弗里德曼这些弄潮儿看不到的?《起火的世界》一开篇,蔡美儿讲述了发生在菲律宾蔡氏家族的一场悲剧,她的姑妈在家中被自己的司机谋杀,割喉致命,正是从悲剧出发,蔡教授提出了贯穿全书的核心概念“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market-dominant minorities)”——一个常见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存在。任何社会,只要存在着这种少数群体,那么市场和民主之间就难免一场结构性的冲突。说的简单些,自由市场偏爱少数人,甚至可能让非我族类的外来者张开掠夺之手,聚敛起巨额财富;而选举民主一人一票,多数人说了算,结果就可能是土生土长的群众选出了一个操弄民粹情绪的政府。这样的态势一旦形成,要么就是市场主宰民主,催生出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要么就是民主摧毁市场,类似多数人的暴政,歇斯底里的群众将怒火发泄在经济精英的身上,情势必要时,甚至肉体消灭之。照理说,民主和市场都是启蒙时代的好东西,但不受节制的市场,再加上没有法治制衡的民主,就可能祸害一方,精英和民众都逃无可逃。
她之视野所及,又有什么是他们看不到的?

《起火的世界》叫好又叫座,让蔡教授在写作的道路上有资本打开脑洞。公允讲,2007年的《帝国之时代》讨论古今中西大国的兴与衰,对蔡教授而言不算越界之作,尤其是在耶鲁这个据说“除了不教法律,什么都教(anything but law)”的法学院内,一个不会写小说的宪法学家是演不好戏剧的(参见“虎爸”鲁本菲尔德)。更何况,真正的学者向来都是问题导向的,活人难道还要被领域框死!2007年前后,“9·11”后第六年,正是法学界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在研究中重新带回“帝国”之时,蔡教授不失时机加入了这场自带流量的焦点讨论。虽然有著名作家罗伯特·卡普兰和哈佛帝国学者奈尔·弗格森背书加持,但读罢《帝国的时代》,我却难掩失望。
两相对比,《起火的世界》有多么政治不正确,《帝国之时代》在学术场域的政治上就有多安全。蔡教授上下五千年,只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帝国如要崛起,制霸自身所知且所在的“世界”,成功的秘诀归根到底是“宽容”,因为人才总是不拘一格而降于各地的,只有做到宽容,国家才能如磁铁一样吸引异邦人才,最终得“天下”英才而用之,则帝国兴焉。但帝国崛起之路上以宽容为本,势必包含着诸多政治部族的多元杂处,话糙理不糙,撕逼的种子早已埋下。终有一天,“政治胶水”无法继续粘合起杂多族群的分歧,多元无法共存于一体,身份政治抬头,每个政治部族都自以为是地追问“我们是谁”,文化内战兴起,帝国也就由此开始了盛极而衰的下坡路。简言之,帝国之命运,成也宽容,败也宽容。
这论题是如此庸常,甚至多少有些陈词滥调,阅读《起火的世界》时那种惊喜感,至此已经所剩无几。但也要承认,就书论书,《帝国之时代》阅读体验并不差,首先是作者写作水准有增无减,故事讲的精彩纷呈,更重要的还在于,蔡教授对“宽容”下了一个非常宽容的定义,并不是非要平等尊重每一个人,包括政治异见分子,才叫宽容(也许在她看来,这种宽容观,本身就是生活在启蒙时代之后自由主义的偏见),“在我运用这个概念时,宽容所指的仅仅是,让极其不同的族群在你的社会里生活、工作并且繁衍下去——即便只是出于工具或战略的理由”,简言之,只要允许百家争鸣,而不是焚书坑儒,那就符合蔡教授的“宽容”尺度。如此一来,社会科学的书呆子也许认为是属于选择偏差的案例,却构成了《帝国之时代》最骨骼清奇的章节。在专章讨论“混血唐朝”作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时,蔡教授给西方读者讲述了一代女皇武则天及其科举取士的国策,“女皇的创新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转折点。新确立的国家考试制度反映出全新的原则,也即政府官员应当仅仅根据教育和文学天赋而获得招录。”[12]下一章,转入讨论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也许是蔡教授自己都觉得这脑洞开的大了些,所以不忘先修辞过渡一下:“请等一下——蒙古人是宽容的?”[13]但论断却没有和稀泥:“成吉思汗推行着相当宽容的政策,即便以现代标准而言都是如此,更不必说与同时代统治者做比较了。”[14]无论以“宽容”作为帝国崛起之谜底的立论是否恰当,是否只是浮光掠影地理解帝国政治,蔡教授似乎没有多加追问,当然也不是我们要关切的。总之,书是好书,也相当成功,这就已足够。美中不足的是此书中文版先后经历数个版本,但直到2016年仍将Amy Chua忠实地译成“艾米·蔡”,两位译者显然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到了虎妈横空出世的第五年,也对这位华裔的耶鲁女教授没有了解一下,哪怕只是问问百度。
跳过《虎妈的战歌》,直接进入作为“战歌”之番外篇的《三件法宝》。但这一次,夫妻合璧,琴瑟合弦,却未能延续“战歌”的成功,也许《战歌》之盛况,原本就是可一不可二。商业上的销量难以摸清虚实,不过这本据两位作者说“提供了一种看待成功之新方式”的书,用学术判准来看,实在写得有些水,让我开卷后几度欲弃书而去。书之开篇,首先交待了美国梦破碎的历史进程,“如果你是出生在1960年之后的美国人,那么你的人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父母是谁”;[15]但问题是,美国梦并非让每个人都心碎,对于某些“文化群体”来说,美国梦仍触手可及。若是属于这些族群部落的成员,只要付出个人的奋斗,就有很大可能走向人生的成功。为什么美国梦偏爱某些“文化群体”,这是《三件法宝》所要回答的问题。
哪些族群呢?虎妈和虎爸就是当仁不让的幸运儿,华裔和犹太裔的身份让他们可以现身说法,继续挖掘个人奋斗和家族浮沉的历史故事,再用文化人类学包装一下呈献给读者。作者之身份就是最牢靠的挡箭牌,不会因看似政治不正确的立论而惹祸上身。无论如何,由少数族群亲口讲述他们为什么能,比起亨廷顿告诫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不要忘本,要时刻牢记“我们是谁”,虎妈的基调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算不上违规。这些成功族群,无论是说与生俱来,还是在后天成长过程中习得,到底有哪些人无我有的文化特征以及行为模式呢,虎妈虎爸反求诸己,总结出走向成功的“三件法宝”。分别传授如下:第一件被称为“优越感”(Superiority Complex),就是要相信自己所在的族群是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我们不一样;第二件是“不安全感”(Insecurity),按照作者的解释,这是“一种不满——关于你在社会中的价值或位置,怀有一种不确定的焦虑”,简言之,明天不一定会更好,有可能更糟糕;第三件法宝则是“冲动之控制”(Impulse Control),对人生要有长远的规划,不能任由一时兴起的念头而主宰自己的举动,比如,不能因为今天的困难而放弃长久的目标。在定义这第三件法宝时,有一句非常鲁本菲尔德教授的话,“活在当下,是现代性的律令,而那些可以控制冲动的人,不是活在当下的。”最终,三件法宝如果在某个群体那里集于一身,那么生为这个群体的人,既有力争上游的动力(优越感+不安全感),又在面对困境时不轻言放弃,自觉坚持下去(优越感+冲动控制)。他们不是活在短促的当下,只寻求一时之满足,为了明天会更好,他们甘愿在今天吃更多的苦。这种风物长宜放眼量的人生态度,对中国人来说,实在太过稀松平常,毕竟三岁小孩都会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甚至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大概就是我读《三件法宝》的感受,即便你们讲的都对,so what?还不是听过很多人生的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终于到了今年2月,虎妈在企鹅出版社推出了她的第五本书《政治的部族:团体冲动与民族之命运》,一如既往,我作为粉丝迫不及待地网购了这本新书。[16]
04
西谚有云:狐狸知道许多事,而刺猬知道一件大事。经柏林之演绎,这句话成为人文社科学界尽人皆知的比喻,如果借这种两分提出我们的问题,那么虎妈到底是狐狸,还是刺猬呢?
种种迹象表明,虎妈分明是一个狐狸,显而易见,她知道许多事。前述四本书,读起来可谓下笔千言,彼此之间却离题万里。何不就此宣判她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学者,在选题上一惯于见风使舵。“9·11”之后谈全球化和帝国政治;中国崛起的新时代转而兜售中国文化,在西方的英文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你看现在,她在新书中又开始讨论政治的“部族主义”,就好像是在说,闪开,让我来告诉你们,特朗普为什么上台。每一步,蔡美儿教授都没有落空,极其精准踩到了时代的热点,只谈这一份敏锐的商业学术嗅觉,在法学界可以说是一时无二。即便同在一个屋檐下,虎爸鲁本菲尔德教授两次越界,就算不上那么成功,若是按照文学作品的销量级数,他那两本小说只能说是不温不火——当然,这丝毫没有影响我对鲁本菲尔德的敬意,虽然他的《自由与时间:关于立宪自治的一种理论》连个平装版都没机会出,但以学术贡献而论,仍是当代最具原创性的宪法理论,哈佛网红教授桑德尔也支持我的看法,他高度评价自己当年课上的助教,认为他的书“将重塑关于美国宪法及其在民主生活中之角色的讨论”,结果虽然真没做到,但学术评价说到底不能仅以成败论英雄。[17]
不抱有任何对狐狸的敌意,我们可否思考另一种可能:在狐狸的表象下,虎妈有颗刺猬的心,是一只披着狐狸外衣的刺猬。蔡教授选题上看似漂移,但在那个刺猬的世界里,反而存在着深层的连贯,是在一个大事上的连击和交响?这么提出问题,并非预设着只有刺猬才是真学者(因此无意为虎妈辩护,她也无需我在此辩护),最终还是回到写作本文的出发点,在中文世界里,虎妈应该怎么读?若是确实存在着另一种读法,那么这种作为刺猬的虎妈能否对我们有新的启示,而不是感受五味杂陈却报一声呵呵了事?
虎妈的论述看似狐狸万变,但却有一个大问题隐匿在其中,由始至终一以贯之,我将之表述为:在全球化时代,多元社会内少数族群的命运。横看成岭侧成峰,一旦这个问题的线索浮现出来,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虎妈。再简单复习一下,《起火的世界》作为虎妈的头生子,她所提出的核心概念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正是这种群体在非西方社会的普遍存在,才制造了自由市场和选举民主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在这本书后,虽然这个概念在蔡教授的笔下消失无踪,但它所对应的那个实体始终是她的主角。
再想一下《帝国之时代》,之所以心思用尽,却只能给出一个平淡无奇的结论,宽容乃帝国崛起之道,也因为少数族群仍是蔡教授的着眼点。在这个刺猬的世界中,《帝国之时代》其实构成了《起火的世界》的续篇,是在历史纵深的维度上对“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追溯。一分为二,帝国如何崛起,讲述的是少数族群在以宽容立国的共同体内得以齐放争鸣的历史阶段,而帝国之衰落,也就对应着帝国无法继续寓杂多于一体,而这不正是一个“起火的世界”的历史剧场版吗?
说到底,是一个“不忘初心”的动人故事

“2009年6月29日,从俄罗斯返回的次日,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也不知道这本书将以何收场”,如按蔡教授所言,从《虎妈的战歌》到《三件法宝》,只能说是她写作一次多少带有偶然的跨界,要不是她和女儿在莫斯科红场餐厅一时意气的冲突,世上本无虎妈,而也许耶鲁法学院多了一位在专业领域内深耕细作的法学家——在那个“要不是……”的时空里,蔡教授写了自己的第三本书,建构了一种新的规范性民主理论,以如何对待“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为中心……但刺猬的世界可没有什么纯粹的偶然,都是一件大事的开花结果,具体地说,《虎妈的战歌》和《三件法宝》都是“主导市场的少数群体”这棵藤上结出的瓜。如果说《战歌》还只是讲述虎妈自己的故事,那么《三件法宝》就已经破题,为什么某些少数族群可以主宰经济市场的命脉,走向成功的人生。这两本书,既可以当作育儿经和成功学来咀嚼,有心人也可以视为文化人类学的作品来翻翻。
只要我们把蔡教授的人生和学术贯通起来,那么虎妈内心的刺猬世界,说到底是一个“不忘初心”的动人故事。她之所以对少数族群的命运如此关切,变着法儿地讨论,就是因为她自己就出身于这种“政治部族”,进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读虎妈,我觉得她有时的喋喋不休反而是如此可爱,不止一次,她讲到父母初至美利坚饿其体肤的困苦岁月,在新英格兰的冬天无钱支付暖气费,只能裹紧棉被取暖,相同的情节在《帝国之时代》和《虎妈的战歌》里都出现过,甚至讲的一字不差。也就是说,虎妈的立论以及她对整个世界的看法,都深深地扎根于她的“部族”出身。这也是虎妈为何如此喜欢讲述她的家族故事,那个东南亚的塑料生产线,不时浮现在耶鲁法学教授的笔下:不仅《虎妈的战歌》和《三件法宝》,《起火的世界》讲述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秩序,却开篇于蔡氏家族的悲剧,她在菲律宾的姑妈在家中被司机割喉,而《帝国之时代》笔下纵横捭阖,开篇同样是虎妈的家务事:“我想我的父母是典型的美国人。他和我母亲都是华裔,但在菲律宾长大。他们孩童时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活在日军枪口下,直到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解放菲律宾。我父亲还记得,他们手舞足蹈,奔跑在美军吉普后,等着美国大兵扔出午餐肉的空罐子。”[18]
“人以群分(Humansare tribal)”,蔡教授的新书《政治的部族》开篇做如是宣告,在此意义上,我把这本书理解为虎妈的一次阶段性理论总结,在前四本以不同的视角甚至文体切入“少数族群”之后,新书终于给出了虎妈的“政治部族”理论。如果看到西方学界近年来关于身份政治的讨论已成新热点,远的不必说,就看在知识界颇有风向标作用的福山先生,也将今年秋季推出他讨论身份政治的新书——《身份:对尊严之需求以及仇恨的政治》,[19]那么我们又很容易把虎妈的第五本书判定为一本跟风之作。如果说本文的讨论想证明什么,那就是虎妈到今日为止的全部论述实有一个贯通的线索:身份的政治,构成了她的刺猬世界里的那个大事。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也是在这一点上,这位华裔女性教授,反而要比大多数白人男性理论家更早地感知到后冷战时代的根本问题,并以自己所选择的讲述方式隐晦地表达出来。我们不能因为她独具一格的表达方式,甚至商业上的成功,就否定虎妈也有自己的理论。在她那个刺猬的世界里,虎妈反而要比见风使舵如福山者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如她在新书内所言,再次回到了《起火的世界》里的判断,“在我们眼中,世界就是地域性的民族国家,陷于根本的意识形态斗争——资本主义 vs. 共产主义、民主 vs. 威权、‘自由世界’vs. ‘邪恶轴心’。因我们意识形态棱镜的遮蔽,我们一次又一次忽视了更为原生性的族群身份,对于世界上数以十亿计的人口来说,族群身份才是最根本也最有意义的,引燃着世界各地的政治动荡。”[20]
读虎妈时,有一些读者会失望,寻理论而不遇,当他们习惯性地期待着社会契约、无知之幕或审议民主时,蔡教授笔下仍是姑妈遇害、女儿叛逆和妹妹患病——这就是虎妈表达自己思考的方式。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她是浅尝辄止的,但反过来说,知道如何适可而止,不正是一种美德吗?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分工,吃哪一碗饭,是老天爷赏赐的,虎妈从一开始也没有立志要做另一个布鲁斯·阿克曼或哈贝马斯。但在那个刺猬的世界里,从《起火的世界》至今,蔡教授关于政治族群的论述,足以让她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敏锐的观察家、评论家和思考者。
一如既往,我期待着她的新书,第六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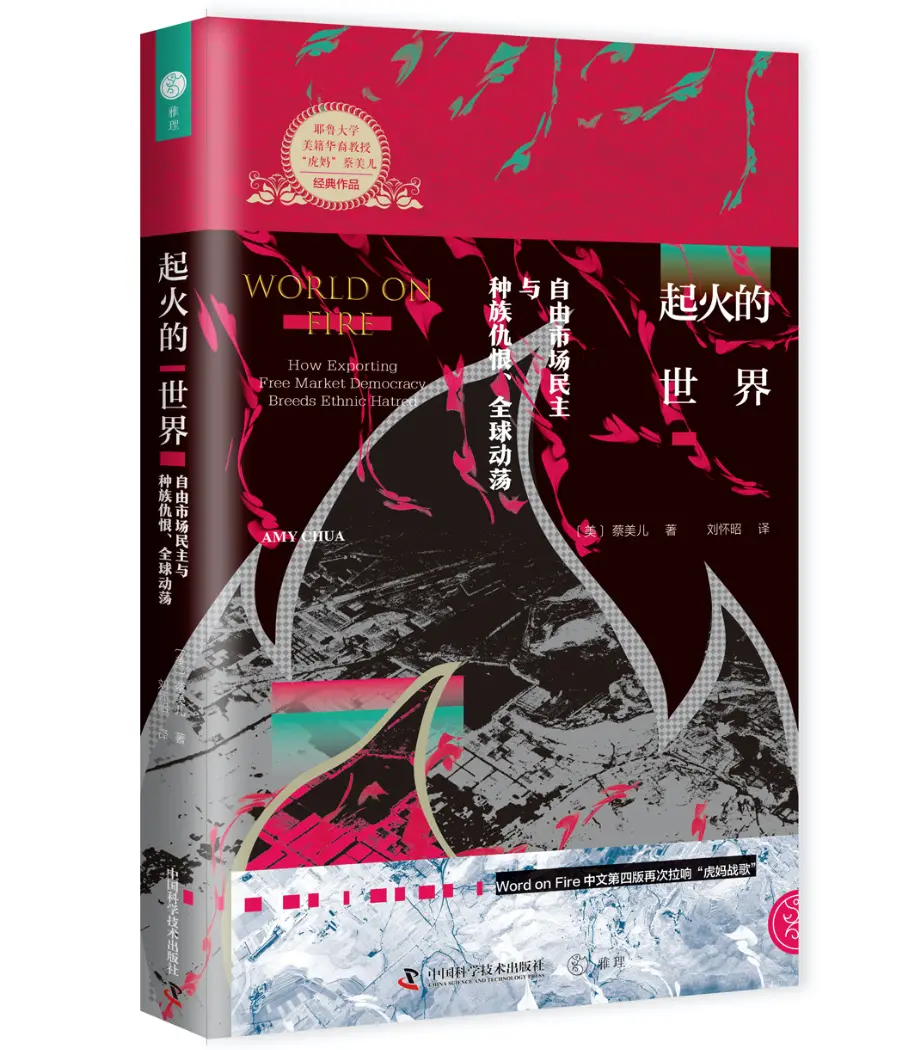
雅理将于2024年8月推出《起火的世界》中文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