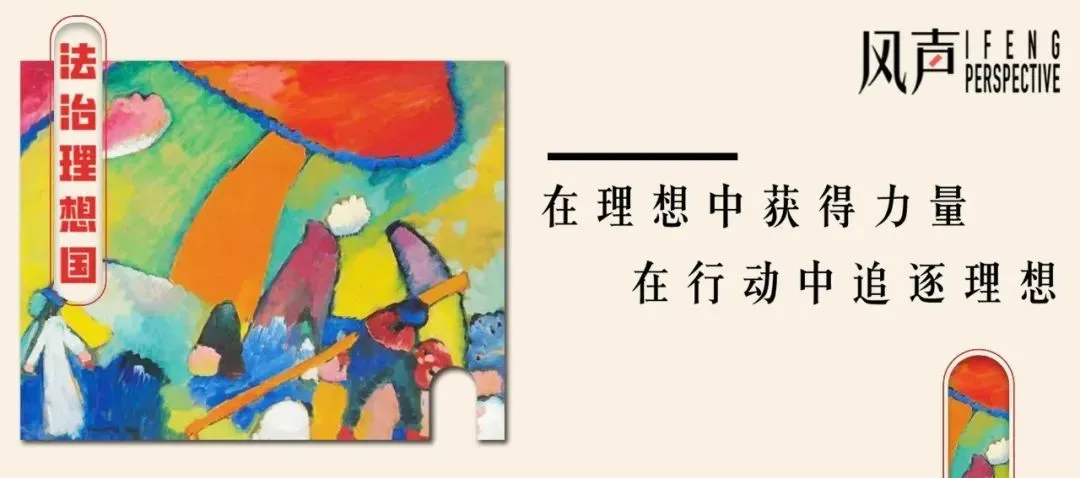
作者| 赵宏
特约撰稿人
近期《中国青年报》又刊出一则人物新闻,一位深圳菜农陈某某16年前,因被广东一名抢劫犯冒名留下了犯罪记录,2014年办理驾驶证时才发现。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于2016年承诺启动纠错程序,并对因信息登记错误而给当事人带来的困扰表示歉意。
令陈某某始料未及的是,今年儿子高考需提前申报志愿时他惊讶地发现,其犯罪记录并未被彻底销毁。迄今,他也只是从湖南老家的派出所拿到了一纸无犯罪记录证明,但曾从事抢劫犯罪并正在服刑的信息,仍旧留存在公安机关的人口数据系统中。在不断奔走反映后,当地公安机关承诺,再等20天就撤销案底。
从2016年至2024年,公安机关既已核实清楚菜农陈某某并无犯罪经历,犯罪记录属于错登,为何消除犯罪记录还会如此艰难?如果真如公安机关所言,20天就可以撤销案底,那为何在启动了纠错程序8年后,陈某的犯罪记录依旧在系统中留存?
这些问题,都引发公众对犯罪记录和违法记录的再度关注。

为何犯罪记录不该永久化?
所谓犯罪记录,是国家专门机关对犯罪人员犯罪事实的客观记载。记载的原因在于对这些曾有犯罪前科者予以特别标记,进而对其特别预防。特别预防的依据又在于,曾有犯罪前科者在法律上会被认为有更大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也会对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全带来潜在威胁。
与犯罪记录互相协同,《刑法》中同样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有过犯罪经历的人,无论所犯之罪是重罪还是轻罪,在入伍和就业时都要向单位报告。又因为目前的犯罪制度并未设计前科的有效期限,这就就造成了前科影响的永久化。
实践中,犯罪记录的影响早已弥散出对有前科者自身参军和就业的限制之外,犯罪人员子女同样会因为父母的犯罪记录而在升学、考公、参军、就业等方面处处受阻,这就是所谓的“一人犯罪,株连全家”。
上述问题,本质上反映的都是重刑主义对我国《刑法》的影响,即仅为公共安全和特别预防的考虑,就对有犯罪前科者及其亲属的权利予以严苛甚至是过度的限制。
这种过度限制,不仅逾越了罪责自负、罪刑相当等法治原则,也对有前科者的社会复归造成了严重障碍。因会产生对犯罪前科者持久的精神羞辱和制度歧视,这种记录已无异于一种现代“墨刑”。
因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和其引发的法治风险,去年12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发布备案审查报告,明确要求取消针对涉电诈犯罪人员的配偶、子女、父母和其他近亲属在受教育、就业、社会等方面的权利予以限制的连坐制度。该审查报告虽仅及于涉罪人员的亲属,但其从宪法基本权利保护出发所强调的“罪责自负”“无罪不罚”的理念,却使冰冻已久的犯罪附随性效果被凿开缝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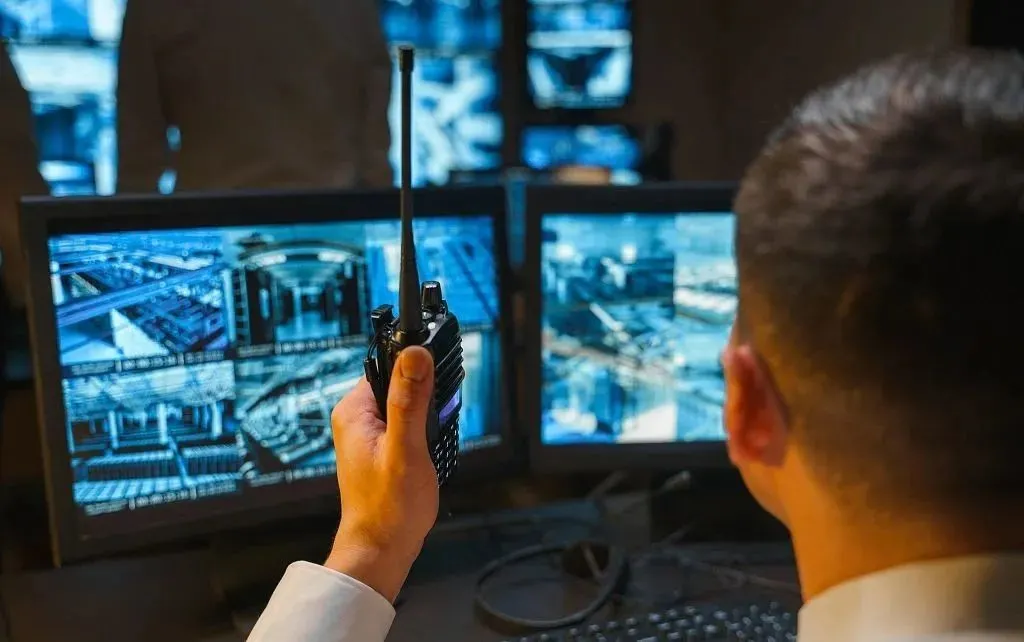
而刚刚过去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其中更明确提及要“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已预示:对有犯罪前科者,我国未来要逐步从目前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逐步扩展到轻罪和微罪的犯罪记录封存,由此避免因“轻罪微罪不轻”、犯罪附随效果沉重所带来的严重违背比例原则和人格尊严的制度实施后果。

犯罪记录,该封存还是该消除?
《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修改后,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问题。而此前发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同样吸纳了这一精神,规定了未成年人违法记录的封存。与彻底消除不同,所谓封存是通过控制和限缩违法记录的查询,尤其是对超出合理范围和合理期间的违法记录,通过禁止查询、披露和使用,来间接达到前科消灭的效果。
例如《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记录封存,就是对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法的人,规定其犯罪记录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的规定,也与此基本类似。上述规定,无疑都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
但从犯罪结构来看,未成年人犯罪只占犯罪人数中很小的比例。这也意味着,所谓封存所产生的禁止查询和披露的效果,对有违法和犯罪前科者的影响都相当有限。
实践中,绝大多数有违法和犯罪前科者仍旧饱受违法和犯罪记录的影响,甚至终身都背负犯罪和违法标签而难以实现社会复归。
而且,封存并不等于彻底消除,即使对未成年人违法和犯罪,《刑事诉讼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也规定了,例如“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例外。
因此,未来除要参照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制度,建立普遍的轻罪和微罪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外,破除现代墨刑更核心的做法,仍旧是考虑建立经过特定时限和特定条件的记录消除和前科消灭制度。
前科消灭和记录消除,不仅有利于扫除轻罪和微罪前科者社会复归的制度障碍,在法理上也有其基础。法政策上对有违法犯罪前科者予以特别标记,是认为这些人有更高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因此要对其予以特别预防。
但对有前科者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的评估,往往并无科学依据,也并不容易被理性作出。很多时候,因为过度追求风险防控,违法和犯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和再犯可能都会被过度夸大,特别预防也由此沦为公权机关倾轧个人权利的口实。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近年因为刑罚圈的不断扩大,醉酒驾、帮信罪已成为人数攀升最快的犯罪类型,但此类犯罪很难认为行为人具有较强的道德可责性,其也不属于像毒品犯罪、性犯罪一样的成瘾性犯罪。因此,不加区分就对这类犯罪前科者实施与其犯罪行为和危害后果都不相符合的附随后果,实在难以证立。
据此,如果违法犯罪人的违法行为情节轻微,社会危害程度不大,其所从事的职业也与其违法犯罪行为本身并无实质关联,就不能再通过行业禁入、权利剥夺甚至是株连亲属等方式再对其进行精神羞辱。
同时,在经过一段时间且符合一定条件,可以确认行为人并无特别的人身危险和再犯可能后,就应对其犯罪记录予以彻底清除。法律也应确立相应的犯罪记录消除机制。

与此类似,治安违法记录的存在,也主要是作为行政处罚的量罚基准和刑事制裁的酌定情节。但无论是作为量罚基准还是酌定情节,法律都有明确的期限限制,过了一年、两年甚至三年,此前的违法记录也应彻底清除而不该再被考虑。

违法犯罪记录被误登后,怎么办?
再回到本案。尽管公安机关早在2016年就确认陈某某的犯罪记录登记有误,但为何迟迟无法消除?
迄今对犯罪记录予以规定的,是两高三部2012年颁布的《关于建立犯罪人员记录制度的意见》以及公安部2021年印发的《公安机关办理犯罪记录查询工作规定》。
尽管上述规范对对犯罪人员信息库的建立、录入的信息内容,甚至如何对犯罪信息予以录入都有相对严格的程序规定,却缺少对记录有误的处置规定,也缺少当事人对错登误登如何救济的规定。
实践中,公安机关在消除犯罪记录方面,也存在很多结构性障碍 :例如,因法院和公安的信息互联,以及公安机关内部刑事侦查信息库和人口管理数据库的信息互通存在问题,法院判决信息常常未及时反馈给公安机关,进而录入到人口数据库。
此外,犯罪记录和违法记录的属性迄今同样不明,这也导致出现诸如错登误登问题出现时,私人究竟应向作为刑事司法监督机关的检察院反映,还是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同样未获厘清。这就导致当事人只能一趟趟地奔走于公安机关,通过反映情况,甚至求助媒体而获得解决。
《中国青年报》的新闻刊发时,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口头通知陈某某其犯罪案底已被撤销,但仍未提供书面证明。而受访的民警也反映,虽然常住人口系统的犯罪记录已被消除,但仍可能存在子系统抓取了陈某某此前的犯罪记录;而无法消除的情形,未来也只能等其发现后,再联系当地公安机关消除。

打破偏见,才是现代法治的诫命
本案中,陈某某还只是未实施过犯罪行为被错登的人员,实践中还有大量确有犯罪违法记录的人员,他们仅因一次轻微的违法和犯罪就终身背负劣迹记录,进而导致在生活和工作中饱受偏见和歧视。
这种做法,实在与现代法治所强调的过罚相当严重抵牾,其本质就是通过对犯错者的持续羞辱来达到震慑违法和社会治理的效果。
但是,这种治理又何尝不是只将个人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和手段,而完全忽视即使是犯错者依旧拥有权利和尊严,依旧也要受到法律保护?这种做法,又如何能与现代法律所倡导的要给违法犯罪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互相符合?

在人类刑罚历史上,对于那些曾犯罪的人,古代不仅会割鼻断臂,甚至还会在脸上刻字以示羞辱。但这种野蛮的做法早已被现代法治所废弃,可让当事人终身背负违法记录,并持续地对其进行精神羞辱和制度歧视,又何尝不是一种更隐蔽的墨刑?
法律的最终目标是打破偏见,克服歧视,绝不是通过设置制度性藩篱强化偏见和制造歧视。法治的核心也在于维护每个人的尊严,这其中同样包含违法犯罪者的尊严。
因此,不过度惩罚报复,不将个人作为纯粹的预防和威慑工具,也不株连无辜者,都是现代法治应当谨守的诫命。
梅因在《古代法》中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一运动,在当下仍旧方兴未艾。
“法治理想国”由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共同发起,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栏目。
主编 | 萧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