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乔治·帕克 译/ 歧路听桥】
新冠病毒到来时,发现了一个基本状况危险的国家,并无情利用了那些状况。腐败的精英阶层,僵化的官僚体制,冷酷无情的经济,四分五裂且心烦意乱的公众,——这些慢性病多年来一直得不到治疗。我们早就学会了别别扭扭地容忍这些症状。得有如此规模的一场大流行病和与这流行病的亲密接触,才能暴露那些症状的严重性,使美国人震惊地意识到,我们眼下属于高风险类别。
这危机要求我们在全国层面快速展开理智的集体行动。但相反,美国的应对是巴基斯坦或白俄罗斯式的,就像是个基础设施败坏、政府功能失调的国家,其一众领导人太过腐败和愚蠢,乃至于无法阻挡大众蒙受苦难。行政分支浪费了无法挽回的两个月准备时间。总统有意视而不见,嫁祸他人,夸夸其谈,谎话连篇。从他的喉舌那里,则冒出一个又一个阴谋论和神奇疗法。一些参议员和企业高管行动迅速,但不是要预防即将到来的灾难,而是要从中获利。当有政府医生试图警告公众有多么危险时,白宫拿走了话筒,把那条消息政治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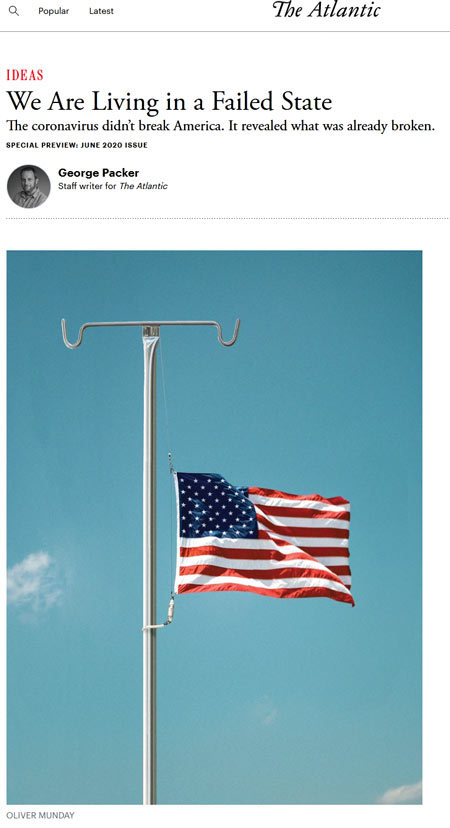
在没完没了的3月间,美国人每天早上醒来,都发现他们自己成了一个失败国家的公民。没有全国性计划,根本没有一以贯之的指导方案:家庭、学校和办公场所都被告知,它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关闭和寻求庇护。检测工具、口罩、医护服装和呼吸机的供应严重短缺,各州州长恳请白宫提供这些物品,遭搪塞后,又向私人企业发出呼吁,而它们无法交货。各州和各市被迫陷入投标大战,这让它们成了漫天要价和企业逐利的牺牲品。民众拿出他们的缝纫机,竭力维持医院工作人员的健康和病人的生机。俄罗斯、台湾和联合国向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国,一个陷入彻底混乱中的乞丐国家,送来了人道主义援助。
唐纳德·特朗普几乎完全从个人和政治角度看待这场危机。因为担心连任,他宣布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为一场战争,而他自己是战时总统。但他令我们脑海中浮现的领袖,是法国将军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etain)元帅。1940年,德国击溃法国防御力量后,贝当与德国签署了停战协议,随后组建了亲纳粹的维希政权。特朗普就像是贝当,与入侵者勾结,将他的国家抛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2020年的美国更像是1940年的法国,已经用一场崩溃令自己目瞪口呆;相较于一位可悲的领袖,这场崩溃来得规模更大、程度更深。
未来,人们在剖析这场大流行病时,可以借用历史学家、抵抗运动战士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对同时期法国沦陷的研究,称其为“不可思议的失败”(Strange Defeat)。
尽管在全美国,个人展示勇气和牺牲的例子数不胜数,但失败是全国性的,而且理当迫使我们提出一个大多数美国人从不曾必须问到的问题:我们是否足够信任我们的领导人和彼此,可以召唤人们以集体方式应对某次致命威胁?我们依旧有能力实施自治吗?
从9·11到金融危机
这是这个短促二十一世纪经历的第三场重大危机。
第一场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那时,美国人从精神上讲还生活在前一个世纪,经济衰退、世界大战和冷战的记忆依旧强悍。那一天,中部农业腹地的民众没有将纽约视作理当承受那般命运的外邦移民和自由派人士的熔炉,而是视作一个为整个国家承受了打击的伟大美国城市。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消防队员驱车八百英里,为在世界贸易中心废墟的救援行动施以援手。市民的本能反应是共同哀悼,齐心动员。
党派政治和危害严重的政策,尤其是伊拉克战争,抹去了国家团结的意识,催生了对精英阶层的怨恨,这种怨恨从未真正消失。发生在2008年的第二次危机加剧了那种怨恨。在最顶层,金融崩溃几乎可以被认为是一次成功。国会通过了一项两党都接受的救助法案,挽救了金融系统。即将离任的布什的行政官员与即将上任的奥巴马的行政官员展开了合作。美联储和财政部的专家们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防止了第二次大萧条的发生。一些最重要的银行家遭到羞辱,但没有被起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保住了自己的财富,一些人保住了工作。没过多久,他们的业务就回归正常。一位华尔街交易员告诉我,那场金融危机早就成了“减速带”。
身处中间层和底层的那些债务缠身,失去了工作、房子和退休储蓄的美国人,感受到了所有挥之不去的苦楚。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从来没有恢复元气,在那场萧条中成年的年轻人注定比他们的父辈更加贫穷。不平等作为197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人生活中的一支基础性的无情力量,变得更加严重了。
第二场危机在美国人中间,在更上阶层和更下阶层、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大都市人和农村人、土生土长的人口和移民、普通美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之间,制造出了深刻的隔阂。社会关系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情况已有数十年,现在它们开始撕裂。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一些改革举措尽管在医保、金融监管、绿色能源等方面意义重大,但仅有权宜之效。过去十年的长期复苏,富了企业和投资者,但欺骗了专业人士,且将工人阶级更远地抛下。经济衰退的持久影响是,加剧了两极分化,令权威,尤其是政府的权威,声誉扫地。
两党都迟迟未能领会到,他们的公信力丧失了多少。即将到来的政治是民粹主义的,其先兆并非贝拉克·奥巴马,而是萨拉·佩林(Sarah Palin),这位毫无准备到荒谬程度的副总统候选人对专业知识嗤之以鼻,并陶醉在名人效应中。她是唐纳德·特朗普的“施洗者约翰”(John the Baptist)。(萨拉·佩林,生于1964年,2006年12月至2009年7月间担任阿拉斯加州州长,是该州历史上最年轻且为女性的州长,共和党人。施洗者约翰,是公元一世纪早期的一位犹太巡回传教者。——译注)
特朗普行政分支:谎言和腐败
特朗普是作为共和党建制派的反对者登上权力宝座的。但保守派精英阶层和这位新领袖之间很快达成了谅解。无论他们在贸易和移民之类问题上有何种分歧,他们的基本目标都是共同的:为谋取私人利益而赤裸裸地开掘公共资产。那些希望政府尽可能少为共同利益做事的共和党政客和捐款人,可以与一个全然不知如何统治国家的政权愉快共处,而且自己充当了特朗普的仆人。
特朗普就像一个在干燥的田野上扔火柴的男孩那样肆意,开始牺牲美国人残存的市民生活。他甚至从来都没有假装自己是整个国家的总统,而是挑动我们,围绕种族、性别、宗教、公民身份、教育背景、地域,以及——在他上任以来的每一天——政党问题,互相争斗不止。他的主要统治工具是谎言。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人将自己锁在一个布满镜子的大厅,认为那就是现实;有三分之一的人因坚持认为真理可知,而自己发疯了;另有三分之一的人甚至放弃了尝试。
持续多年的右翼意识形态攻击,两党都在推动的政治化,加上持续的资金缺乏,已严重戕害特朗普斩获的联邦政府。他开始着手摧毁总统这项工作,破坏专业的公务员队伍。他赶走了一些最有才华和经验的职业官员,留下一些重要岗位无人填补,并安插了忠于他的人士充当政委,凌驾于饱受恐吓的幸存者之上,目的是:服务于他自己的利益。他的主要立法成果是减税法案,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行动之一,这部法案为大企业和富人送去了数千亿美元。受益者成群结队,到他的度假胜地消费,排队为他的连选提供资金。假如撒谎是他运用权力的手段,那么腐败就是他的目的。
这就是呈现在新冠病毒面前的美国景观:在繁荣的城市,一群与全球各处联络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依赖一群朝不保夕、隐匿无形的服务业工人;在农村地区,衰败的社区反抗着现代世界;在社交媒体上,不同阵营之间充斥着相互仇恨和无休无止的谩骂;在经济领域,尽管就业充分,但成功的资方和受困的劳工之间存在巨大且不断拉大的差距;在华盛顿,一个由骗子和他智力破产的政党,在领导一个无效的政府;在这个国家各个地方,弥漫着一股愤世嫉俗的疲惫情绪,你看不到人们有共同的身份或未来。
假如这场大流行病真的是一种战争,那么这将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第一场。侵略和占领暴露了一个社会的断层线,夸大了在和平时期被忽视或被接受的东西,澄清了基本的真相,扬起了被掩埋的腐烂气味。
不平等与政治体的败落
这病毒本应当将美国人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威胁。假如领导层不同,美国人是可能被团结起来的。相反,即使病毒从民主党主政的地区蔓延到了共和党主政的地区,人们的态度依旧沿着我们熟悉的党派分界线分裂了。
这病毒也本应成为一个重要的平衡因素。要成为病毒的攻击目标,你不必在军队服役,也不必负债累累,而只需要是一个人。但从一开始,病毒的影响就被我们容忍太久的不平等扭曲了。在几乎不可能找到病毒检测方法的时候,富人和有关系的人——模特和电视真人秀节目主持人海蒂·克拉姆(Heidi Klum),布鲁克林网队(Brooklyn Nets)的全部候选队员,总统的保守派盟友——就能以某种方式获得检测机会,尽管许多人没有症状出现。这样的个人零星检测结果对保护公众健康毫无帮助。
与此同时,有发烧和发冷症状的普通人不得不排在漫长且可能已被感染了的队伍中等待,但只是被拒之门外,因为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一个网络笑话提议,要想知道你是否感染了病毒,唯一的办法就是对着富人的脸打喷嚏。
当被问及这种明目张胆的不公正时,特朗普表达了不赞同的意见,但补充说:“也许这就是生活。”正常时期,大多数美国人很少注意到这种特权。但在这场大流行病爆发的最初几个星期,如此特权引发了公愤,就好像在一次总动员期间,富人被允许出钱免服兵役,并囤积防毒面具。随着这场传染病的扩散,其受害者已经可能是穷人、黑人和棕色人种。美国医疗卫生系统的严重不平等,从公立医院外排队运送尸体的冷藏车可以明显看出。
我们现在有两类工作:必不可少的工作的和非必不可少的工作。谁是必不可少的工人?主要是从事低薪工作的人,那些工作需要他们本人在场,会直接危及他们的健康:仓库工人、填充货架的工人、在Instacart为网上下单者买东西并交付的人、送货司机、市政雇员、医院工作人员、家庭护理工人、长途卡车司机。医生和护士是抗击这场大流行病的英雄,但配有瓶装消毒液的超市收银员和带着乳胶手套的联邦包裹公司(UPS)司机,是保持前线部队完好无损的供应和后勤部队。(Instacart是一家技术公司,创办于2012年,在美国和加拿大运营,提供当日食品杂货的送货和取货服务。——译注)
在隐匿了各阶层人类的智能手机经济中,我们正在学习的是,我们的食物和商品从哪里来,是谁让我们活着。在亚马逊生鲜配送(AmazonFresh),下单一份有机婴儿芝麻菜很便宜,且可以隔夜送到,这部分是因为,种植、分类、包装和运送它们的人在生病期间必须继续工作。对大多数服务业的工人来说,病假是一种不可能的奢侈。值得追问的是,我们是否愿意接受更高的价格和更慢的交货速度,这样他们就可以呆在家里了。
这场大流行病也明确了,谁才是非必不可少的工人。一个例子是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新晋参议员凯莉·吕弗勒(Kelly Loeffler),她1月份之所以能填补空缺的议员席位,唯一的资质是她的巨额财富。上任不到三个星期,她参加了一次有关新冠病毒的可怕的秘密简报会,之后抛售股票,从中获得了更多财富。然后她指责民主党夸大了危险,并向她的选民做出了错误的保证,这大有可能害了他们。吕弗勒在公共服务方面展示的冲动,是那种危险寄生虫的冲动。一个可以让这样的人担任高级职务的政治体,已经败落到了较晚期。
库什纳与特朗普行政分支的崩溃
政治虚无主义最纯粹的体现不是特朗普本人,而是他的女婿兼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库什纳被欺骗性地宣传成了精英和民粹主义者。
1981年,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那个月,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房地产商家庭,是第二镀金时代的太子党。尽管学业成绩平平,但在其父查尔斯(Charles)承诺向哈佛捐赠250万美元后,贾里德仍被哈佛大学录取。父亲用1000万美元的贷款帮助儿子创办了家族企业,然后贾里德继续在纽约大学的法学院和商学院接受精英教育,他父亲向这里贡献了300万美元。2005年,查尔斯因利用妓女构陷其妹夫并拍下了这次会面,试图用这种办法解决家族法律纠纷,而被判入狱两年,当时贾里德以强烈的忠诚回报了他父亲的支持。
贾里德·库什纳曾拥有一栋摩天大楼,并办过一份报纸,都未获成功,但他总能找到人来拯救他,而且他不过是越来越自信。安德烈·伯恩斯坦(AndreaBernstein)在《美国寡头》(American Oligarchs)一书中描述了他如何采纳了一位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即新经济“破坏者”意见的故事。在导师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影响下,他找到了融合财务、政治和新闻业追求的门道。他将利益冲突当成了自己的商业模式。(默多克,1931年生于澳大利亚,美国传媒业大亨。——译注)
因之,随着其岳父成为总统,库什纳很快就在一个将业余行为、裙带关系和腐败升级为统治原则的行政分支中获得了权力。只要他忙于中东和平,他那些没有意义的介入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就并不重要。但自从他成为对特朗普有重要影响的新冠病毒事务顾问以来,结果就是大规模的死亡。
3月中旬,上任后第一周,库什纳参与撰写了记忆中最糟糕的椭圆形办公室演讲稿,打断了其他官员的重要工作,或者已经违反了安全协议,参与到了涉嫌利益冲突且违反联邦法律的事项中,并做出了很快就化为乌有的愚蠢承诺。“联邦政府的设计不是要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他在解释他将如何利用自己的公司关系,在免下车餐厅(drive-through)设立核酸检测点时这样说。那些关系从未落到现实中。一些企业领导人说服他相信,特朗普不应动用总统的权威强迫一些产业生产呼吸机。后来,库什纳自己试图与通用汽车谈判达成协议,但未能实现。他对自己没有失去信心,于是将必要设备和装备短缺的责任算到了不称职的州长头上。
看到这位面色苍白、身材苗条的票友闲庭信步般介入一场致命的危机,抛开了商学院的行话以掩盖他岳父的行政分支的巨大失败,就相当于看到了整个统治方式的崩溃。事实表明,科学专家和其他公务员并非叛国的“阴谋势力集团”(deep state)成员:他们是必不可少的工人,将他们边缘化,以理论家和谄媚者取代,是对国家健康的威胁。事实表明,“灵活”的公司无法为灾难做好准备,也无力分发救生物资,只有能干的联邦政府可以做到这一点。事实表明,所有事情都有代价;经年累月地攻击政府、榨干政府资源、消耗政府的士气,造成的沉重代价是公众不得不付出生命。
所有项目都被撤资,所有库存都被耗尽,所有计划都被取消,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成了一个二流国家。然后,病毒和不可思议的失败就来了。
危机时刻的抉择
制服这一大流行病的战斗也必须是恢复国家健康并重建它的战斗,非如此,我们眼下正忍受的苦难和悲痛就将永远得不到补偿。
有目前的领导层,什么都不会改变。如果说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耗尽了人们对老一代政治当权派的信任,那么2020年就应当碾灭“反政治”是我们的救星的念想。结束这个政权,是必须的和值得的,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我们面临一个选择,这场危机让这个选择变得清晰到了无可逃避的地步。我们可以长期保持自我隔离,惧怕和回避彼此,让我们共同的纽带消失殆尽。
抑或,我们可以利用正常生活中的这种停顿,留意一下:那些举着手机,好让他们的病人可以和亲人说再见的医院工人;那些从亚特兰大飞去纽约帮忙的一飞机医务人员;那些要求把他们的工厂改造成呼吸机生产厂的马萨诸塞州航空产业工人;那些因无法通过电话联系到人手稀少的失业办公室,而排着长队的佛罗里达人;那些无惧没完没了的等待、冰雹和传染,在党派立场强烈的法官强加给他们的选举中投票的密尔沃基居民。
我们可以从这些可怕的日子中领会到:愚蠢和不公正是致命的;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充当公民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团结的替代品是死亡。走出藏身之处,摘下口罩后,我们不应忘记一个人独处是什么滋味。
(本文转载自《大西洋月刊》,是美国最受尊敬的杂志之一,创办于1857年。作者是美国《大西洋》杂志特约撰稿人,著有《 Our Man: Richard Holbrooke and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和《The Unwinding: An Inner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本文原题“Underlying Conditions”,见于《大西洋》杂志2020年6月号,提前发布的网络版题为“We Are Living in aFailed State”。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


